战犯抑或恐怖分子更合适? 战争罪和反恐立法的比较研究
引言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与恐怖主义相关的法律越来越多。自2011年叙利亚战争爆发,以及伊斯兰国(IS)组织成立后鼓励年轻人离开自己的国家、主要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加入他们的战斗以来,掀起了一股立法浪潮,规定取消公民身份、禁止与恐怖分子和恐怖组织相关联、指定世界上某些地区禁止公民前往,并扩大域外管辖权。虽然反恐立法可能会提出国际人权法关切, 1 但它也对继续尊重国际人道法(IHL)造成了重大问题,因为许多罪行都发生在武装冲突期间或与武装冲突有关。
特里斯坦·费拉罗(Tristan Ferraro)在本期《红十字国际评论》的文章中谈到了围绕反恐立法的国际人道法问题,以及国际人道法保留条款(即必须根据国家现有的国际人道法义务来解读立法)和人道豁免(使人道工作者可以继续在所谓的恐怖主义控制区工作)的必要性。2 本文并不是要重复费拉罗文章中的国际人道法定义和讨论。作为对他的文章的补充,本文探讨了当国家围绕恐怖主义采取一系列立法措施并开始以恐怖主义罪行起诉个人时,通常应该(作为国际人道法的执行机制)适用的战争罪相关法律被忽视的风险。
那些去叙利亚和伊拉克作战(外国战斗人员)然后返回自己国家(无论他们在何处被允许这样做)的人,有时(但并不经常)根据反恐立法受到起诉,因为他们被怀疑为被本国标识为恐怖分子的武装团体或组织作战。然而,他们可能曾作为一个通常以使用非法作战手段和方法作为其战略的一部分而闻名的某一方的成员或与之并肩作战。3 他们可能犯了战争罪。有人主张要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为此类外国战斗人员设立一个战争罪法庭, 4 但这种想法尚未实现。起诉仍然是国内法的事项: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更倾向于以恐怖主义罪行而不是以战争罪起诉?
凯科巴德(Kaikobad)指出,“战争罪……是违反战争法规和习惯的罪行,……然而,恐怖主义行为……并不违反国际法。这些行为基本上是对国内法的违反,而这些法律源自各国原则上可以加入也可能不加入的国际条约。”5 他接着说,如果一个人严重违反了日内瓦四公约 6 并犯下了恐怖主义罪行,则根据国际法,一个国家有义务以战争罪而非恐怖主义罪行进行起诉。 7 如今,我们会将日内瓦四公约的共同第3条、《第二附加议定书》和习惯国际法规定的起诉战争罪的义务扩大为起诉严重的国际罪行,此类罪行应予调查,并在有证据的情况下予以追诉和惩处。 8
然而,正如特别报告员菲奥努拉·D. 尼·伊兰(Fionnuala D. Ní Aoláin)在本期《红十字国际评论》的采访中所说:
对各国来说,特别是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背景下,将行为者及其行为视为恐怖主义性质,而不是去评估日内瓦四公约共同第3条和《第二附加议定书》的适用性可能意味着什么这样更困难而复杂的问题,是非常方便的。9
本文采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了阿富汗、澳大利亚、马里、荷兰和俄罗斯联邦这五个国家是否有能力起诉战争罪和恐怖主义罪行,以及如果它们同时具备处理反恐罪行和战争罪的能力,它们是否应该优先考虑战争罪?之所以选择这些国家,是因为它们代表了不同的地区;它们都有通过其他国家的恐怖组织参加武装冲突的公民;并且已经或正在发生武装冲突或卷入武装冲突。这些国家都批准了大多数相关的国际人道法条约,因此除了习惯国际法产生的义务外,它们还担负起诉战争罪的相应义务。10
本文从理论和法律的角度研究了起诉的价值和影响是什么。最终,将提出战争罪起诉是否应优先于恐怖主义起诉以及什么因素阻碍了这种起诉的问题。11
背景设定:恐怖主义罪行和战争罪能否同时发生?
有哪些战争罪行被记录在案?
战争罪是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 12 它是指严重破坏日内瓦四公约和《第一附加议定书》(国际性武装冲突)、严重违反共同第3条和《第二附加议定书》(非国际性武装冲突),13 以及其他严重违反战争法的行为,如(在国际性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攻击平民或民用物体。14 日内瓦四公约得到了普遍批准;本文研究的五个国家都是《第一附加议定书》缔约国,其中四个国家是《罗马规约》缔约国。因此,它们都有义务起诉和惩罚严重破坏日内瓦四公约和《第一附加议定书》以及严重违反共同第3条的人。此外,习惯国际人道法当然适用于所有国家,它要求对上述所有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进行调查、追诉和惩罚。15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以在平民居民中散布恐怖为主要目的的暴力行为或暴力威胁”在国际性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都属于战争罪。 16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前南刑庭)在“加利奇”(Galic)案中表示, 17 虽然他们不考虑该罪行的习惯法性质,但根据1992年的协定法,存在一种在平民居民中散布恐怖的罪行,其要件如下:
-
暴力行为针对平民居民或未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平民个人,并导致平民居民死亡,或身体或健康受到严重伤害。
-
罪犯故意使平民居民或未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平民个人成为这些暴力行为的对象。
-
实施上述罪行的主要目的是在平民居民中散布恐怖。 18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罗马规约》)19 在第8条中列出了一份庞大(但并非详尽无遗)的战争罪清单,其中(分别)述及国际性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并将严重破坏日内瓦四公约和《第一附加议定书》的行为与违反共同第3条和其他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区分开来。需要注意的是,《罗马规约》不包括“以在平民居民中散布恐怖为主要目的的暴力行为或暴力威胁”,尽管此类行为可能部分包含在故意指令攻击平民居民的行为中。 20 鉴于前南刑庭在加利奇案中能够将对平民居民的攻击与恐怖行为视为两个独立的指控,因为法庭认定两者都构成了现行的战争罪,这是一个有趣的发展。
有充分资料显示,最近在外国战斗人员前往的伊拉克和叙利亚发生的武装冲突中,发生了针对平民居民的恐怖行为,包括大规模屠杀平民、强奸;此外,在我们的两个重点国家——马里和阿富汗,除了其他战争罪行,还发生了造成被拘留者死亡,对其实施酷刑以及残忍和不人道待遇的情况。21 可以举一些例子来证明,在上述每一个司法管辖区中都有可能同时以恐怖主义罪和战争罪进行定罪。澳大利亚、阿富汗、马里、荷兰和俄罗斯联邦的公民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为列入名单的恐怖组织作战,无论是伊斯兰国组织还是他们的敌人。联合国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发现冲突各方都存在以下违法行为:屠杀和其他非法杀戮、任意逮捕和非法拘留、劫持人质、强迫失踪、酷刑和虐待、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非法攻击、使用非法武器、围困以及任意和强迫流离失所。22 在伊拉克,2014年至2016年期间,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L)在摩苏尔犯下的罪行包括处决宗教少数群体、涉及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的罪行以及针对儿童的罪行。 23 据报道,与叙利亚和伊拉克国民相比,外国战斗人员更有可能更多地参与极端暴力行动。 24
国际刑事法院(ICC)正在对马里和阿富汗进行调查。在马里,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称,有合理的理由相信在马里发生了以下罪行:战争罪,包括谋杀;残伤肢体、残忍待遇和酷刑;故意指令攻击受保护物体;未经正规组织之法庭之宣判而遽行判罪及执行死刑;抢劫;以及强奸。25 在阿富汗,检察官办公室认为,“谋杀;残忍待遇;损害个人尊严;未经适当的司法授权而遽行判罪和执行死刑;故意攻击平民、民用物体和人道援助任务团;以及背信弃义地杀害或伤害敌方战斗员等战争罪行”26 已经发生。
并非所有的恐怖主义罪行都是作为战争罪或武装冲突的一部分,或与之同时发生。在许多情况下,那些被判定犯有恐怖主义罪行的人并没有实施任何实际行动,而是实施了犯罪的预备行为;此外,许多被判犯有国内罪行的人是不会在武装冲突期间实施任何行为的,因为战争罪仅适用于存在国际性或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情况。因此,本文所考虑的情形仅涉及人们前往或驻扎在发生武装冲突的地方的情形。此外,正如费拉罗在本期《红十字国际评论》中指出的那样,27 那些在和平时期实施的、可被指控为恐怖主义罪行的行为,如果它们是合法的战争行为,则可能不属于战争罪。相反,并非所有的战争罪都是出于恐怖主义意图或由恐怖组织成员实施的, 28 本文也不考虑这些罪行。
被归类为恐怖分子的人实施的行为能否在国内以战争罪被起诉?
如上所述,战争罪严重违反了国际人道法,是整个国际社会所关切的罪行。然而,尽管具有国际性,但实际上,作为一个合法性原则的问题,除非国内立法赋予法官进行判决以及检察官和警察进行调查的相关权力,否则各国都不能以战争罪起诉个人。虽然所有国家都有义务颁布立法,起诉所有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但这五个国家并非都有相关的战争罪国内立法,赋予它们起诉所有战争罪的实际能力。《阿富汗刑法典》(2017年)、《澳大利亚刑法典法》(1995年)附表《刑法典》和《俄罗斯联邦刑法》(1996年)允许对战争罪和恐怖主义罪行进行起诉(下文将对所有重点国家的恐怖主义罪行进行考量),并且可以累积起诉(即可以同时提出多项指控供法官裁定)。将战争罪和恐怖主义罪行纳入同一部法律可能会促进对这两种罪行进行起诉的能力。然而,在澳大利亚,总检察长必须以书面形式批准对战争罪的起诉,29 而非恐怖主义罪行的起诉。这可能会给检控考量增加政治因素。30 鉴于恐怖主义罪通常被认为更具政治色彩,这似乎是一个奇怪的区别。
马里和荷兰对恐怖主义罪行另行制定了立法。31 它们都可以累积起诉。荷兰已经这样做了,下文将对此进行解释。这表明,即使并非同一部法律,但只要检察官知道存在这些法律,战争罪和恐怖主义罪行也就可以同时被起诉。
重点国家里有四个是《罗马规约》的缔约国,因此有一些立法来确保它们能够根据补充性原则,包括《罗马规约》第17条关于可受理性的要求,在本国进行起诉。32 澳大利亚和荷兰纳入了《罗马规约》的所有罪行,并对国际性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作了同样的区分。阿富汗和马里纳入了《罗马规约》的大部分罪行。但阿富汗没有区分国际性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只是加入了一个特别条款,主要是针对违反共同第3条的行为。马里主要禁止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犯罪,尽管其措辞方式表明,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某些犯罪与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犯罪相同。
然而,由于这些国家遵照《罗马规约》规定的罪行,它们就无法起诉 “针对平民居民的恐怖行为”;它们的国内法都没有规定该罪行。这对澳大利亚来说尤为奇怪,因为在“加利奇”案中,法庭在决定恐怖行为是否属于国际法规定的现有罪行时所考虑的立法之一就是澳大利亚1945年的《战争罪法》,该法早于后来将其取代的《刑法典》纳入战争罪的时间,并将“系统性恐怖主义”列入其战争罪的范畴。 33
因此,这些国家将不得不依靠诸如强奸和其他性暴力、34 残伤肢体、 35 攻击平民、 36 攻击参与人道援助或维持和平任务的人员或物体37 或者酷刑,38 才能将所谓的恐怖分子作为战犯绳之以法。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国家有能力处理所谓的恐怖分子可能参与的犯罪行为,然而,尽管这四项立法中的战争罪清单看似很长,其中也仍存在很大的缺失。
俄罗斯联邦不是《罗马规约》的缔约国, 39 其《刑法》 40 也没有照搬日内瓦四公约或附加议定书(俄罗斯是其缔约国)中的战争罪。其《刑法》第356条禁止虐待战俘和平民居民、驱逐平民居民、在被占领土上劫掠国家财产,以及在武装冲突中使用俄罗斯联邦缔结的国际条约所禁止的手段和方法(其中包括《特定常规武器公约》及其议定书、《化学武器公约》以及《生物武器公约》规定的所有武器,当然还有《第一附加议定书》的敌对行动规定和严重破坏日内瓦四公约和共同第3条的行为)。这一最后条款确保了与攻击平民和使用某些武器(例如,可以说是简易爆炸装置)有关的一系列重要罪行被纳入俄罗斯法律。俄罗斯联邦也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41 和《禁止酷刑公约》 42 的缔约国,这两项公约似乎对一系列的罪行作出了规定。
以在叙利亚、伊拉克、马里和阿富汗可能犯下的被控战争罪为例,所有五个重点国家都有能力以某种方式起诉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劫持人质、强奸、酷刑、残伤肢体、攻击平民、使用某些类型的武器和攻击人道工作者(以及其他许多已经犯下并已纳入立法的罪行)都可以被起诉和惩罚。43 仍然引人注目的是,上述国家都没有能力起诉武装冲突中的具体恐怖行为,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在某些武装冲突中的恐怖主义罪行案件中战争罪可能被忽视的原因。接着,下一节将讨论这五个国家是否也能起诉相关的恐怖主义罪行。
根据五个重点国家的立法,所谓的恐怖主义行为是否可以以恐怖主义罪行被起诉?
虽然有理由说恐怖主义罪行实际上是国际罪行,因为它们存在于国际公约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UNSC)的决议中, 44 但是战争罪的区别在于它们是具有普遍定义的罪行。众所周知,恐怖主义罪行受到不同定义和政治解读的影响。45 几十年来,国际社会一直试图通过《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的全面公约》, 46
1. 本公约所称的犯罪,是指任何人以任何手段非法和故意致使:
(一)人员死亡或人体受到严重伤害;或
(二)公共或私人财产,包括公用场所、国家或政府设施、公共运输系统、基础设施或环境受到严重损害;或
(三)本条第一款第二项所述财产、场所、设施或系统受到的损害造成或可能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而且根据行为的性质或背景,行为的目的是恐吓某一人口,或迫使某国政府或某国际组织实施或不实施某一行为。
在现代语境中,这一定义似乎非常局限于特定的暴力行为。如今,恐怖主义罪行的范围远远超出了暴力行为,还包括出于实施此类行为之目的的筹备、训练、出行以及其他作为或不作为。从下文五个重点国家的例子中可以部分看出这一点。尽管如此,与暴力相关的传统恐怖主义概念实际上更自然地符合上述所谓的恐怖分子在武装冲突中犯下的各种战争罪行。正是新型恐怖主义罪行,如列入名单地区的立法(限制前往某些列入国内或联合国名单上的恐怖分子控制的地区),造成了与国际人道法相关的其他问题,包括人道组织的准入和活动。
有趣的是,《全面公约草案》中最有争议的方面似乎是围绕条约对武装冲突的适用性问题。47 草案第20条48 提出一个问题:人们为了实现反对占领者这一政治目标而行动时是否行使自决权,以及如果他们从事类似恐怖主义的活动,是否应根据该条约的国际刑法制度予以起诉。主席的案文试图在武装冲突期间和和平时期使用恐怖主义之间找到平衡。其内容如下:
武装冲突中武装部队的活动,按照国际人道主义法所理解的意义,由国际人道主义法予以规定,不受本公约管辖。
伊斯兰会议组织建议将该案文改写如下:
武装冲突中、包括外国占领情况下各方的活动,按照国际人道主义法所理解的意义,由国际人道主义法予以规定,不受本公约管辖。 49
国际社会面临的挑战在于无法就“武装部队”的定义达成一致意见。另一个问题是,当 “武装部队”对平民的交战攻击构成条约所定义的和平时期的恐怖主义时,是否也能以所谓的“国家恐怖主义 ”的罪名对其提出起诉。 50 同样,就国际人道法的 “保留条款”做出决定,要求检察官以战争罪而非恐怖主义罪行起诉行为人,仍然是一个难题。
与恐怖主义有关的国际程序的另一个例子是黎巴嫩问题特别法庭,它是为武装冲突以外的罪行而设立的。尽管是有争议的,51 但该法庭确定存在一种跨国恐怖主义罪行,现已成为习惯国际法。52 该法庭的上诉庭规定,恐怖主义罪行的习惯法定义需要三个关键要件:(i)实施犯罪行为(如谋杀、绑架、劫持人质、纵火等)或威胁实施这种行为;(ii)意图在民众中散布恐惧(这通常会造成公共危险)或直接或间接胁迫国家或国际当局采取某种或不采取某种行动;(iii)该行为涉及跨国因素。法庭极力强调,他们对习惯国际罪行的定义只适用于和平时期,而不是武装冲突。他们提到了国内法院也对和平时期的习惯国际罪行作了界定。 53 除了围绕和平时期是否存在习惯罪行的争议外,该定义强烈地遵循了与暴力和特定恐怖意图有关的恐怖主义罪行的传统概念。该定义增加了跨国因素,即应该有国际性的一面,或在两个或更多国家行动, 54 这似乎与有时需要起诉本土恐怖主义的情况不相协调。事实上,该法庭的目的是处理黎巴嫩的国内犯罪。
恐怖主义罪行通常是涉及个体国家的安全的罪行,由每个国家决定它们希望如何界定这些罪行。五个重点国家的情况也是如此。虽然本文所述的因恐怖主义罪行而被起诉的大多数情况都发生在可能提起诉讼的国家的领土之外,但这些国家都有能力对仅发生在其领土上和仅针对其政府的恐怖主义罪行进行起诉,而无需涉及国际或跨国层面。它们也都有能力起诉在和平时期和武装冲突时期犯下的恐怖主义罪行,因此,诸如特别法庭所作的区分并不适用。
事实上,可被归类为“恐怖主义”的罪行范围很广。虽然与暴力有关的罪行更符合上文讨论的战争罪类型,但可以说,罪行种类繁多会使起诉恐怖主义罪行更加容易。恐怖主义罪行的范围可以包括从加入恐怖组织,到向恐怖组织或相关人员提供援助、物质支持、培训和财政支持等各种类型。恐怖主义犯罪还可以包括立法,规定人们不能前往那些据称由恐怖组织控制的指定地区。而且,此类犯罪通常要求有特定的恐怖主义意图。
《澳大利亚刑法典》第100条第1款将恐怖主义罪行定义为以下行为:
(a) 造成严重伤害,即对人的身体伤害;或
对财产造成严重损害;或
(c) 导致某人死亡;或
(d) 危及某人生命,但并非采取行动之人的生命;或
(e) 对公众或部分公众的健康或安全造成严重风险;或
(f) 严重干扰、严重破坏或毁坏电子系统,包括但不限于:
(i) 信息系统;或
(ii) 电信系统;或
(iii) 金融系统;或
(iv) 用于提供基本政府服务的系统;或
(v) 用于或由基本公用事业使用的系统;或
(vi) 用于或由运输系统使用的系统。
行为出于如下特定意图:
推动政治、宗教或意识形态事业;且采取行动或威胁的意图是胁迫或通过恐吓影响联邦或某一州、领土或外国,或某一州、领土或外国的部分地区的政府;或恐吓公众或部分公众。
《澳大利亚刑法典》第101条远远超出了与暴力有关的行为的传统概念,规定了一系列的恐怖行为,例如提供或接受恐怖行为的培训,或出于恐怖行为的目的拥有或编写文件。第102条规定了与恐怖组织有关的罪行(根据《刑法典法》和相关条例规定),包括加入、招募、培训、资助和提供支持。第119条规定了入侵外国领土的行为,跨国因素由此介入。该条还包括“部长确信被列入名单的恐怖组织正在外国某地区从事敌对活动”并宣布此地区为禁区,而行为人仍然进入这一地区的罪行。澳大利亚确实有一些“人道豁免”,允许人道组织开展活动,但没有国际人道法保留条款。
荷兰《刑法典》第83a条同样规定:
“恐怖主义意图”应理解为意图在一国居民或部分居民中引起恐惧,或非法迫使公共当局或国际组织采取或不采取某些行为或容忍某些行为,或严重扰乱或破坏一国或国际组织的基本政治、宪法、经济或社会结构。
荷兰立法将 “恐怖主义意图”作为一种量刑工具,以增加对诸如以下罪行的刑罚:煽动暴力或犯罪行动(第131条和第132条),招募(第205条),伪造(第225条),威胁使用公共暴力(第285条),意图造成恐怖主义犯罪的盗窃(第311条第1款第6项),盗窃和暴力(第312条第2款第5项),敲诈或勒索(第317条和第318条),贪污(第322条),欺诈(第326条),以及破坏财产、数据、电信网络、供水、车辆和货物(第350条~第352条)。在这方面,立法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专门针对传统的暴力犯罪和资助恐怖主义的某些方面。
马里的法律反映了其所加入的国际恐怖主义公约。马里2016年3月17日第2016-008/号法(规定了打击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的统一法)第1条规定恐怖主义行为是:
任何在武装冲突局势中旨在杀害或伤害平民或未直接参与敌对行动的任何其他人,且依其性质或背景旨在恐吓民众或迫使一国政府或国际组织采取或不采取任何行动的行为。
这项特殊的法律严格遵照《全面公约草案》和特别法庭对恐怖主义的传统定义,但没有规定国际人道法保留条款或人道豁免条款,因而该法不能根据国际人道法进行解释,并由此要求以战争罪(如适用)而非恐怖主义罪行起诉。
2008年7月23日关于在马里打击恐怖主义的第08-025号法规定了一系列罪行,如危害飞机安全、在飞机上实施暴力、在海上和陆地破坏车辆、盗窃核材料、攻击基础设施或信息服务等罪行。这些是域外犯罪,也适用于马里境内。
2017年《阿富汗刑法典》规定了以下恐怖主义罪行(在阿富汗境内外为了影响阿富汗政府或外国政府或国家或国际组织的政治事务,或破坏阿富汗或外国政府系统的稳定(第263条)):劫持人质(第270条)、绑架(第267条)、自杀式爆炸(第265条)、使用爆炸物(第266条),破坏基础设施(第269条)、使用或转让核材料(第268条)、杀害和攻击应受国际保护的人员(第271条)、危害航空罪(第272条~第276条)、加入恐怖组织和与之合作(第277条),以及资助恐怖活动(第279条)。这些罪行再次倾向于与暴力有关的恐怖活动的传统定义,且没有包含国际人道法保留条款。
《俄罗斯联邦刑法典》比上述其他一些例子更为宽泛,将下列恐怖行为定为犯罪(第205条):为恐怖活动提供便利(第205条第1款),公开煽动恐怖主义、为恐怖主义辩护和宣传恐怖主义(第205条第2款),开展恐怖主义活动培训(第205条第3款),组织和参与恐怖主义团体和恐怖主义活动(第205条第4款和第205条第5款),不报告恐怖主义行为或进行虚假报告(第205条第6款和第207条),劫持人质(第206条),劫持飞机、水运或所有铁路车辆(第211条),武装叛乱(第279条),公开呼吁极端主义(第280条),攻击享有国际保护的个人和实体(第360条)以及国际恐怖主义行为(第361条)。跨国或国际因素显然对其他罪行而言并不构成一个问题。该法典没有规定国际人道法保留条款,并且有些方面具有相当的政治性。例如,不报告恐怖主义罪行的行为似乎是为了确保媒体在对可能参与武装冲突的人员进行报道时采用特别的表述,将其称为恐怖分子,而非战斗员。
在更传统的意义上,根据《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205条,恐怖主义是指实施爆炸、纵火或其他行为,恐吓民众,并造成死亡、重大财产损失或其他严重后果的风险,以扰乱政府机构或国际组织的活动或影响其决策;以及威胁采取这些行为来影响政府或国际组织的决策。
这些罪行中有一些涉及与上述战争罪相关的人身行为,但正是由于有能力指控某人为恐怖组织成员或与恐怖组织有关联,才能够在几乎不审查他们所从事的活动的情况下起诉大量人员。虽然反恐立法不如战争罪立法统一,但所有五个国家都有能力以一系列反恐罪行起诉从叙利亚或伊拉克返回的任何人。在下一节中,本文将讨论事实上是否有人因战争罪或恐怖主义罪行而被起诉,之后一节将考虑是否存在与此类起诉相关的一些政治、哲学和道德问题。
是否有以战争罪和恐怖主义罪行而被起诉的情况?
既然已经确定在叙利亚、伊拉克、马里和阿富汗有犯下战争罪的情况,以及在所研究的五个国家中的每一个国家均有人犯下了恐怖主义罪行,接下来与此相关的问题就是:是否有人根据现行法律受到了起诉?
2015年至2020年期间,全球有超过10055 起因恐怖主义罪行被定罪的记录。在国内,有2556 人因战争罪被起诉。由于对此类罪行的起诉的有限性,这个数字可能更准确。如果加上国际法庭的起诉数量,这一数字将增加到27人。57 为了便于比较,表1显示了恐怖主义罪行与战争罪的定罪数量的对比。58
表1. 五个重点国家的起诉数量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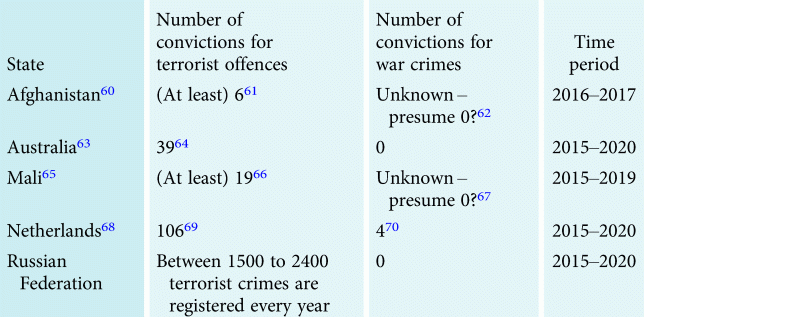
表1中的参考资料
| 国家 | 恐怖主义罪行的定罪数量 | 战争罪的定罪数量 | 时间段 |
|---|---|---|---|
| 阿富汗 60 | (至少) 6 61 | 不明 – 推测为 0? 62 | 2016–2017 |
| 澳大利亚 63 | 39 64 | 0 | 2015–2020 |
| 马里 65 | 至少19 66 | 不明 – 推测为 0? 67 | 2015–2019 |
| 荷兰 68 | 106 69 | 4 70 | 2015–2020 |
| 俄罗斯联邦 | 每年有1500至2400起恐怖主义罪行被登记在案 | 0 | 2015–2020 |
大多数国家最初的做法是鼓励人们首先不要离开自己的国家,这也是几起起诉发生的地方。例如,澳大利亚实施了一些诸如公民身份要求的限制措施, 71 阻止公民或前公民回国。据报道,虽然俄罗斯有特别多的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作战的人员,但他们只接受了少数人回国,而且迄今只起诉了其中的少数人。 72 另据报道,在叙利亚武装冲突的早期,车臣士兵主要是在回国后因雇佣军罪行而被起诉。73 就在最近,另一个消息来源表明,起诉更多的是为了阻止人们离开俄罗斯。74
在荷兰,第一个从叙利亚回来后被判犯下恐怖主义罪行的人也被判犯有谋杀和非预谋杀人罪,他被发现曾在叙利亚与恐怖组织一起训练和战斗。75 这些谋杀和非预谋杀人罪的定罪本可以根据叙利亚的局势来考虑,并升级为战争罪。荷兰正在开始增加与战争罪相关的指控。2019年,一名荷兰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在一名挂在十字架上的死者旁摆出笑脸。他因加入恐怖组织和损害个人尊严的战争罪(不人道和有辱人格地对待尸体)而被起诉和定罪。 76 荷兰正在考虑其他一些此类案件。
美国国会图书馆报告称,“2014年10月,俄罗斯南部的一家法院将一名〔在叙利亚〕战斗中受伤后回国的俄罗斯国民逮捕并判刑,〔同时〕针对据信在叙利亚作战的人在缺席的情况下启动了三起刑事案件,而另一家省级法院则下令将一名当地居民的名字列入国际通缉名单”。77 目前尚不清楚这些案件是否也涉及战争罪。
澳大利亚的做法也是更倾向于防止人们离开该国和资助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活动,而不是在他们回国后起诉他们。 78 上述参考文献中引用的统计数据来自2014年,但实际上从2015年以来出国的人数确实已经减少了。 79 此外,到2018年,布朗(Braun)报告称,“在大约30名回国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中,没有人因为与出国支持恐怖主义组织有关的罪行而在澳大利亚被定罪”。80
在马里,虽然特别司法小组(在检察官办公室主管所有与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最近被授予了起诉战争罪的权力,但它还没有对战争罪提起过诉讼。在阿富汗,虽然有许多针对国内恐怖主义罪行的起诉,但并没有关于起诉外国战斗人员的统计数据,尽管最近的一篇新闻报道表明,有408名来自其他国家的伊斯兰国组织成员被阿富汗拘留。81
本文考察的所有五个国家的立法都表明,无论是在其境内还是在海外犯下的战争罪和恐怖主义罪行,都可以被起诉。这当然更困难,而且一国更希望起诉在其境内而非海外犯下的罪行可能也有其他原因,下文将对此进行探讨。相关人员似乎没有被以战争罪起诉,而有些人则被以恐怖主义罪行起诉。很少发生起诉这一事实是有原因的。如果能够以战争罪起诉他们但却没有起诉,这就引出了两个进一步的问题。首先,相对于恐怖主义罪行,以战争罪起诉有什么好处?其次,此类起诉面临哪些挑战?以下两节将讨论这些问题。
究竟为何起诉?
有人不禁要问:为何一个国家要对战争罪或恐怖主义罪行进行起诉?正如德伦布尔(Drumbl)所指出,关于为何国家(和国际法庭)对战争罪等大规模暴行犯罪进行起诉和惩罚的学术研究很少。82 他研究了历史上和当代的惩罚和量刑方法,特别是基于他从事的与大规模暴行受害者相关的工作。
关于战争罪,德伦布尔概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受害者和胜利者两种对立观点的挑战。这一框架最终围绕解决“罪恶”问题,人们认为这在国际刑法中是可以实现的。83 纽伦堡法庭和东京法庭的规约强调,报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因战争罪被起诉的人进行判决的理由之一。84 正如内米茨(Nemitz)所说,“量刑判决隐含镇压的目的,即主要战犯……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因此他们将受到应得的惩罚。”85 他指出,这些审判只处理最高级别的罪犯,任何改造的希望或其他审判的理由都不适用。 86 他接着研究了前南刑庭和卢旺达刑庭的规约,并指出这两个法庭的组织决议表明它们“在量刑方面采取了更为镇压性的政策”。 87
哈费茨(Hafetz)在谈及关塔那摩监狱囚犯(他认为应该以战争罪而不是国内战争罪或恐怖主义(或特别设立的)罪行来起诉)的待遇时指出,“对被拘留者采取严厉的、往往是残酷的待遇是以这样一个理论为前提的,即他们不属于日内瓦四公约规制的范围,因为他们是非国家恐怖主义组织的成员或支持者。”88 在这方面,《哈佛法律评论》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发生之后写的一篇社论表明,美国政府以发动战争回应这些袭击是因为刑事程序不被认为是 “令人满意的”(本文作者不同意这种做法,但将其作为分析历史上对恐怖主义所做应对的基础)。89 其论点是,一些恐怖袭击被认为是如此严重,以至于需要进行实质性的报复。如果恐怖袭击发生在有关国家的领土上,影响更为直接,这一点可能尤为重要。90
报复性司法与“罪有应得”的理念相关联。它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罪犯“理应”为自己的错误而受到惩罚,而且所施加的惩罚的严厉程度应与他们所犯罪行的严重程度相称。 91 如下所述,大多数惩罚理论的特点是强调预防犯罪,由威慑、改造和使之丧失犯罪能力的理论共同推动。92 报复(或司法的报应理论)的核心前提是惩罚是一种报复形式,如果你犯了不法行为(尤其是严重罪行),你就应该受到惩罚,即使这种惩罚不会有任何其他益处或产生任何其他好处。 93 德伦布尔概述了起诉儿童兵在这方面面临的挑战。关于翁格文(Ongwen),他指出,有些人认为他受到的惩罚已经足够了,因为他受到的待遇与他所施于他人的相同;而另一些人则声称他应该为自己实施的暴行而付出代价。 94 克拉克(Clark)和凯夫(Cave)则更进一步,拒绝将报复作为惩罚战争罪犯罪者的理由,因为“不可能进行相称的报复”。 95
克拉克和凯夫更倾向于将威慑作为起诉战争罪的一个理由。96 内米茨指出,前南刑庭和卢旺达刑庭的规约将威慑作为惩罚的目的之一,97 早期的判例也表明了惩罚战争罪犯罪者的这一理由。 98 威慑经常被用作惩罚的动机,其依据是对罪犯实施惩罚将防止或阻止其他人在未来犯罪。99 它被视为一种预防性动机。知悉犯罪活动会受到惩罚和法律处罚,应该会对那些可能正在考虑犯罪的人起到抑制作用。正是对法律处罚的恐惧,才有可能使人避免做出被禁止的行为。同样,在起诉反恐罪行方面,布朗说:
在这一领域引入和修改刑法的根本目的主要在于威慑个人今后不从事恐怖主义行为,以及通过证明其他打算支持恐怖主义组织的人的行为将产生包括监禁在内的(严重)法律后果,从而对其进行震慑。100
另一个可能的起诉理由是使罪犯丧失犯罪能力,克拉克和凯夫也赞成将此作为起诉战争罪的理由。101 这与国家负有确保保护公众的责任有关。其理由是,监禁(或其他形式的惩罚,如软禁或控制令)将使罪犯丧失行动能力,使他们在一段时间内无法犯罪,从而防止日后犯罪。102 这一点值得注意,因为反恐犯罪也关系到国家和公民的安全。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曾表示:
不出所料,〔外国战斗人员〕被认为是对其本国的一个重大威胁。……人们担心的是,一旦他们回国,他们将会利用自己所受的恐怖主义训练来策划和实施袭击、建立新的恐怖主义小组,或以其他方式促进未来恐怖主义行为。……联合国第2178号决议呼吁各会员国将前往(或试图前往)其他国家参与策划或实施恐怖行为的国民绳之以法。因此,需要在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回国后立即采取协调行动,以确保获取任何可找回的证据,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提出起诉。103
如果以监禁为目标,刑罚可能会对起诉战争罪还是恐怖主义罪行的决定产生影响。在阿富汗,根据《刑法典》第277条被判定为恐怖组织成员的人将被判处 “长期监禁(5年以上至16年)”。直接攻击的战争罪将被判处死刑或一级持续监禁(20年至30年以上);使用某些武器将被判处二级持续监禁(16年至20年以上);强奸、其他性暴力、使人陷于饥饿和招募儿童将被判处5年至16年以上的 “长期监禁”。104 在俄罗斯,对恐怖主义罪行的处罚是终身监禁;对战争罪的处罚是20年监禁。《马里刑法典》第32条规定对所有战争罪罪犯判处死刑。导致人员死亡的恐怖主义罪行将被判处死刑,其他恐怖主义罪行将被判处最高十年的刑期。在荷兰,对严重破坏日内瓦四公约和《第一附加议定书》的行为以及性暴力和背信弃义行为的刑罚最高可达30年。其他战争罪的刑期最长为15年。同样,对恐怖主义罪行可判处15年至30年的监禁。在澳大利亚,对战争罪可判处十年至无期徒刑,视具体罪行而定;对于恐怖主义罪行,适用同样的量刑幅度。从本质上讲,对战争罪和恐怖主义罪行的处罚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因此,在决定以何种罪行起诉罪犯时,这可能不是一个很大的考量因素。
荷兰表示,他们对回国的外国战斗人员的主要关切是通过一系列不同的措施“遏制这一威胁,防止这一现象出现任何新的激增”。105 澳大利亚称回国的外国战斗人员问题是 “国家安全的首要任务”。 106 霍伊费尔特(Højfeldt)也说,“国内刑法正越来越多地适用于武装冲突时期的〔外国战斗人员〕行为。政策目标不再是镇压战争罪,而是保障国家安全”。107
起诉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结束有罪不罚的现象。结束有罪不罚现象一般是针对战争罪等国际犯罪而言的。例如,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目标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对于整个国际社会关注的最严重犯罪,绝不能听之任之不予处罚”,缔约国“决心使上述犯罪的罪犯不再逍遥法外,从而有助于预防这种犯罪”。108 劳埃德(Lloydd)还表示,未能起诉外国战斗人员(以及国家对其国民采取的其他行动),“在避免战争罪不受惩罚方面,可能不利于确保对国际人道法的尊重”。109
国际人道法规定了一项基本义务,即必须起诉那些犯下最严重违法行为的人。日内瓦四公约要求缔约国起诉和惩罚那些违反了关于破约行为条款的人。普遍管辖权适用于此。因此,世界上每个国家都应该能够起诉任何涉嫌严重破坏日内瓦四公约的人:“各缔约国有义务搜捕被控为曾犯或曾令人犯此种严重破坏本公约行为之人,并应将此种人,不分国籍,送交各该国法庭”。如果它们不能起诉涉嫌战争罪的人,则应将其引渡到可对其进行战争罪起诉的地方。其理念是,战争罪如此严重,以至于影响整个国际社会,因此国际社会应负责确保这种罪行不再发生。
联合国通过大量安理会决议倡导对恐怖主义罪行进行立法。例如,2014年,安理会第2178号决议决定,会员国“应确保本国法律和条例规定严重刑事罪,使其足以适当反映罪行的严重性,能够起诉和惩罚”“资助、筹划、筹备或实施恐怖主义行为”之人。然而,这些罪行本质上仍然属于国内事项:每个国家都以不同的方式处理这些罪行,而事实上,国家从未就制订一项“国际反恐公约”达成共识。在提起公诉从而结束有罪不罚的现象和承认这些罪行影响整个国际社会这方面,各国之间缺乏相同的根本推动力。因此,在试图将关塔那摩军事委员会与国际战争罪起诉区分开来时,哈费茨曾说:
罪行的严重程度、所服务的多个社区,以及对可行起诉的数量所作的资源和政治限制,使国际刑事司法与国内起诉有所不同。被起诉的罪行和定罪后的判决都充满了象征意义。以战争罪和其他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为由实施的制裁,有助于构建历史叙事,并在世界范围内植入规范价值。这些制裁也表达了国际社会的愤慨之情。110
他的论点是,军事委员会本不应该用国内罪行来起诉关塔那摩囚犯所犯的严重罪行,而应该考虑到国际人道法规定的战争罪。他认为,以恐怖主义罪行起诉与以战争罪行起诉,不具有同样的象征意义和国际价值。
结束有罪不罚现象也与上文讨论的报复和威慑的目标密切相关。前南刑庭在“德拉利奇”(Delalic)案中认为,“对高级政治官员和军官的惩罚将表明,这些官员不能藐视国际社会的制度设计和禁令而不受惩罚”。他们将此说成是一种威慑。111 国际刑事法院的加丹加分庭反映了这种意图,承认:
受害者及其家人表达的对真相和正义的合法需求……发挥着双重作用:(i)惩罚性,作为“社会对犯罪行为和其实施者的谴责的表达”和 “承认对受害者造成的伤害和痛苦的一种方式”,这将抑制任何复仇的欲望;以及(ii)威慑性,旨在“使那些计划实施类似犯罪的人转移其目标”。112
在起诉犯有战争罪的人时,人们也希望看到受害者的故事被公开反映,希望所发生的事情的真相得到表达,希望受害者得到承认。事实上,正如促进对达伊沙/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所犯罪行追究责任的联合国调查组组长对联合国所说:
这种对问责的呼吁不是为了报复,而是为了正义。那些与调查小组交谈过的人希望公开和客观地揭露伊黎伊斯兰国的罪行,以便世界能够看到这些行为的真实性质,并使我们能够共同纪念受害者。证人和幸存者在提供陈述时,一直强调他们不是寻求报复,而是寻求协助使他们所遭受的痛苦得到承认,并将罪犯绳之以法。113
这种方法通常被称为预防性司法,并被视为能够恢复和平。正如前南刑庭在“德拉利奇”案中所说,惩罚是“使该地区恢复和平的有效措施。虽然长期监禁不是理想的做法,但在某些情况下,为了确保该地区的持续稳定,可能有必要对被告判处长期监禁。”114
总体而言,有一些适用于战争罪和恐怖主义罪行的起诉理论。报复、威慑和使之丧失犯罪能力都被用作起诉战争罪和恐怖主义罪行的理由,而在起诉国的领土上发生战争罪或恐怖主义袭击的直接攻击时,报复的理由可能更强。与预防和结束有罪不罚现象有关的其他起诉理论似乎与战争罪更为相关。可能确实存在反对以战争罪起诉的论点。在这方面,纳斯泰夫斯基(Nastevski)认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澳大利亚在进行战争罪审判方面的经验大体上不尽人意”。115 他将此归因于缺乏起诉居住在澳大利亚的战犯的愿望或政治意愿,同时他指出澳大利亚“在参与各种国际社会努力,引入对国际罪行的问责时,使用了适当的道德措辞”。116
最后,对以战争罪还是恐怖主义罪行进行起诉的决定,很可能取决于哪种理论在政治上更具有分量。劳埃德指出:
除了遵守法律义务外,一系列政策原因促使各国对外国战斗作出反应。这些原因可能包括维护国家声称的对合法使用武力的垄断、支持避免加剧暴力的立场、希望保护国民免受可能的伤害,或避免因国民卷入外国武装冲突而造成外交政策失误或领事问题。与此相关的是,从外交定位和国内辩论中可以看出,各国最关心的往往是国内的安全问题,即潜在的和正在回国的外国战斗人员的行动可能造成的问题,而不一定是战斗人员在目的地国的行为和对国际人道法更普遍的尊重的问题。117
在本节的结论中,对战争罪的起诉增加了结束有罪不罚现象和伸张正义这一道德层面的意义。有人提出,如果起诉战争罪不利于司法公正,则战争罪也不应该受到惩罚。在这种情况下,和解方法可能更适合。恢复性司法与和解可能适合于正处于战争状态的一国境内。而马里和阿富汗将是这种做法的候选国家,尽管由于持续的武装冲突,目前几乎没有机会启动正式的进程。就外国战斗人员而言,和解方法也不适合目前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发生的所谓恐怖主义活动。在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情况下,应该根据国际人道法进行调查和起诉,因此恢复性司法也是不合适的。
起诉工作面临哪些挑战?
除了前几节所考虑的道德和政治因素外,起诉工作可能面临法律和实际挑战,从而导致政府考虑以战争罪还是以恐怖主义罪行进行起诉。一个实际的考量因素是检察官和法官能否查阅到相关法律,尽管本文所讨论的五个国家似乎不存在这个问题。在这五个国家中,有三个国家将这些罪行列入《刑法典》中,因此检察官和法官都可以查阅。荷兰对这两种罪行都有定罪,这些罪行规定在不同的法律之中,但这似乎并不影响对它们的查询。马里也有两项独立的法律,但同一个检察官办公室负责根据这两项法律进行起诉。
其他实际考虑因素可能包括进行起诉所需的证据类型。实际上,无论战争罪还是恐怖主义罪行,收集证据都具有挑战性。布朗指出,对于恐怖主义罪行,“在国内刑事法庭上确定任何……罪行所依赖的证据将是由国际情报机构收集的证据……情报信息可能是从未知或非法来源收集的,并且经常受到审查,由于存在安全风险而不能全部提供给被告”。118 一些非政府组织为起诉目的收集证据,但往往 “这些类型的人权组织的报告属于一种特殊的类型:……它们是为活动家的目的而写的,而其方法与一种专门的调查性新闻报道最具可比性”。119 平民正义中心曾说:
逮捕嫌疑人并不是在战争期间进行起诉面临的唯一挑战。采访仍然生活在叙利亚的受害者和证人也成问题。此外,检察官需要获得书证和物证,而专家调查员和法医分析人员可能也无法获得这些证据。 120
曾为荷兰政府做过研究的鲍克内赫特(Bouwknegt)也认为,在海外收集战争罪和恐怖主义罪行的证据具有挑战性,因为那里有“不同的政治制度和结构;其他安全制度和结构;其他法律制度、结构和传统;其他经济制度和结构;以及其他基础设施 ”。121 他还补充:“法医和直接目击者的证据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再也无法获取。”122 在这方面,关于外国战斗人员,布朗引用了一名澳大利亚联邦警察的话:
逮捕行动是在被指控的罪犯从叙利亚返回后很久才进行的……原因是收集证据有困难……从五年多来一直是战区的叙利亚收集证据几乎是不可能的,警方也不得不等待从美国的社交媒体公司获得的电子证据。123
澳大利亚试图起诉据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巴尔干地区武装冲突中犯下战争罪的人。在两个值得注意的案件中,当时的证据法要求证人前往澳大利亚出庭作证,但他们因为年迈或生病无法前往。由于缺乏证据,案件无法继续审理。124
目前,由于一份报告提出了特种部队在阿富汗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指控,澳大利亚正在开展战争罪调查。125 它所面临的挑战包括证人可能受到非国家武装团体的报复。126 平民权利中心也指出,保护证人是世界各地起诉叙利亚境内和从叙利亚回国的战斗人员的一个问题。 127
与战争罪或更复杂的恐怖袭击相比,单纯的恐怖主义罪行,例如加入恐怖主义组织,可能更容易收集证据。国际审判组织(TRIAL International)说:“证明对恐怖主义的指控,特别是恐怖主义组织成员的身份,是非常简单明了的。只要与已知的恐怖分子有联系或前往恐怖主义组织控制的地区,就能确保定罪。” 128
尽管如此,战争罪的特殊性质及其价值129 应该得到承认,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予以起诉。有人提出,战争罪指控可以“补充和扩大指控”,事实上,在荷兰,随着累积指控的采用,这种情况已经开始出现。130 费拉罗在本期《红十字国际评论》中建议各国在立法中规定一个“国际人道法保留条款”,这将使恐怖主义罪行也能够按照国际人道法得到适用。131 这些条款要求按照国际人道法来解读立法,因此,当战争罪与恐怖主义罪行一起实施时,检察官可将前者作为武装冲突中的特别法。同样,范珀克(Van Poecke)等人在审查相关判例法时认为,如果立法中存在一个排除条款,“限制与武装冲突有关的活动可以构成恐怖主义罪行的程度”,那么非国家武装团体成员实施的任何行为都不应被视为 “恐怖主义”,而应根据战争罪立法进行评估。132 考虑到希望结束有罪不罚现象和维护所有国家都遵守的法律,国际人道法也应成为首选,因为它对犯罪的背景有正确的定义和理解。国际人道法还规定了不应有诉讼时效和大赦,这意味着可以在犯罪发生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对其进行起诉,这与犯罪的严重性是相一致的。劳埃德认为,未能起诉外国战斗人员(以及国家对其国民采取的其他行动),“在避免战争罪不受惩罚方面,可能不利于确保对国际人道法的尊重”。133
战争罪的起诉需要对国际人道法和国际刑法有一定的了解,以证明与武装冲突的关联,而这当然与恐怖主义罪行的起诉无关。凯科巴德认为,被指控的战犯和恐怖分子都会设法利用这种关联进行辩护:在被以恐怖主义罪行起诉时,他们会以此关联为由称自己是合法的战斗人员;而在被以战争罪起诉时,则会称与武装冲突之间不存在关联。134 然而,从相关的国家实践和颁布的刑法来看,目前的恐怖主义罪行似乎不享有战斗人员豁免权。因此,当有人被指控犯有恐怖主义罪行时,国家这样做的原因似乎是认为他们不是合法的战斗人员。在谈到各国对参与需要执行的新的恐怖主义条约的谈判犹豫不决时,迪克斯(Deeks)也提出了同样的看法:“传统上,国际人道法的基础是冲突各方之间对称的法律义务,以及对交战各方之间大致对等的待遇的预期。〔现在〕各国——合理地——并不期望得到那些非国家武装团体的对等待遇。”135 还有一个相关的关切是恐怖主义罪行与本身可能犯有战争罪的国家工作人员没有关系。136 如果开始调查战争罪,可能就需要对冲突双方或各方进行清算。
也许这种方法是各国希望以恐怖主义罪行而非战争罪进行起诉的另一个原因;各国不认为战斗人员是合法的,所以不愿意对他们进行战争罪审判,从而使他们被认为是合法的。采用这种方法,他们可以把身为恐怖主义组织成员的人称为 “恐怖分子”,因此也就称为“其他人”,而不考虑他们所从事的实际活动。
各国可能关心的一个相关问题是,战争罪与司法保障并存,司法保障以如此严格的方式确保公平审判权利,以至于不对起诉者进行合法审判就是一种战争罪。虽然人权和宪法会赋予公平审判的权利,但对恐怖分子的起诉可以援引豁免和国家安全关切;137 事实上,这也是以恐怖主义罪行起诉的数量多于战争罪起诉的另一个需要考虑的原因。
结论
本文提出了一个核心问题,即在外国战斗人员和某些国家境内目前存在武装冲突的背景下,战争罪和实施国际人道法的立法是否以及为什么会因为反恐立法而被忽视。澳大利亚、阿富汗、马里、荷兰和俄罗斯联邦的立法特别适合处理一系列恐怖主义罪行,特别是那些适用于武装冲突时期的罪行,如暴力行为。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它们都有能力起诉和惩罚那些被禁止的恐怖组织的成员。它们不太有能力起诉和惩罚那些犯有相关战争罪的人。例如,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处理恐吓平民居民的战争罪。然而,它们都有相当全面的战争罪立法,可以涵盖看来是由被列入名单的恐怖组织犯下的相关罪行。建议各国应审查其战争罪立法,以确保它们规定了有效的罪行来处理被列入名单的恐怖组织成员在武装冲突中犯下的、原本构成战争罪的罪行。
虽然提出了上述建议,但依然值得再次强调的是数据的匮乏,以及保留有恐怖主义罪行或战争罪起诉的相关数据的地区之少。恐怖主义罪行和战争罪都面临着在武装冲突中起诉(马里和阿富汗)以及必须从海外收集证据(在所有五个国家中都有可能)的挑战。话虽如此,绝大多数案件依然是恐怖主义案件而非战争罪。凯科巴德说:“在许多情况下,恐怖主义行为实际上是战争罪的一种,这一事实将导致适用战争法规和习惯法,而不是吸收了专门领域公约的国内法。”138 目前许多国家似乎没有遵循这种做法。
国际审判组织就优先起诉恐怖主义罪行而非战争罪行的现象指出,“这表面上看是一个程序细节,实际上反映了一种深刻而令人忧虑的法律趋势,这种趋势产生了多种后果。”139 在许多情况下,两种类型的起诉在程序、道德和理论上都具有相同的要求;两者都适合于报复、威慑和使之丧失犯罪能力的理论。在所研究的所有五个国家中,对这两种类型犯罪的处罚都是相当的,因此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两种类型的犯罪都可能导致对犯罪者的惩罚、威慑和监禁。
那么,为什么各国选择以恐怖主义罪行进行起诉?这一定是政策、法律和道德上的微妙差异造成的:以恐怖主义罪行起诉更加方便、更加强调报复和使之丧失犯罪能力,而且还具有强调起诉恐怖分子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附加价值。尽管如此,如果各国不希望看到国际人道法受到侵蚀,也不希望看到结束对最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的有罪不罚现象的持续重要性,它们就应该在每次面临选择时认真考虑这种情况:以战争罪还是恐怖主义罪行进行起诉会更好?战争罪是国际社会,即所有国家,都达成一致并对其需要履行相关基本义务的罪行。因此,在考虑到起诉面临的挑战的同时,应优先考虑以战争罪进行起诉,以确保这一适用于武装冲突的重要法律体系得到尊重和维护。本文表明,对于很多国家来说,对武装冲突中与恐怖主义有关的活动进行战争罪起诉是可能的,它们所面临的挑战几乎与恐怖主义罪行起诉相同。现在是各国认真考虑以战争罪起诉从而结束有罪不罚现象的时候了。
- 1例如,见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关于在打击恐怖主义的同时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工作,载:https://www.ohchr.org/zh/special-procedures/sr-terrorism/issues-focus(所有互联网参考资料均于2021年9月访问)。
- 2关于更详细的分析,请参考特里斯坦·费拉罗在本期《红十字国际评论》的文章:“Counterterrorism, Sanctions and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ICRC Perspectives on Finding the Right Balanc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2021。
- 3Lydia Khalil and Rodger Shanahan, “Foreign Fighters in Syria and Iraq: The Day After”, 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 2016, pp. 2 and , available at: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publications/foreign-fighters-syria-and-i….
- 4See, e.g., Peter Cephas Dahabreh,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Prosecution of Foreign Fighters Responsible for Serious Violations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Committed in the Territory of the Syrian Arab Republic since 2011”, SSRN, 11 March 2019, available at: https://ssrn.com/abstract=3350683 or http://dx.doi.org/10.2139/ssrn.3350683.
- 5Kaiyan Homi Kaikobad, “Crimes against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Acts of Terrorism and Other Serious Crimes: A Theory on Distinction and Overlap”,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Review, Vol. 7, No. 2–3, 2007, p. 213.
- 6《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75 UNTS 31(1950年10月21日生效)(《日内瓦第一公约》),第50条;《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改善海上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及遇船难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75 UNTS 85(1950年10月21日生效)(《日内瓦第二公约》),第51条;《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75 UNTS 135(1950年10月21日生效)(《日内瓦第三公约》),第130条;《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75 UNTS 287(1950年10月21日生效)(《日内瓦第四公约》),第147条。
- 7K. H. Kaikobad, above note 5, p. 214.
- 8让-马里·亨克茨和路易丝·多斯瓦尔德-贝克:《习惯国际人道法第一卷:规则》,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剑桥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中文译本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组织编译,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简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习惯法研究》),规则158,载:https://ihl-databases.icrc.org/zh/customary-ihl/v1/rule158。
- 9“Interview with Fionnuala D. Ní Aoláin”, available at: https://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international-review-of-the-red….
- 10英国和美国制定了完善的反恐法律,并在其法院以恐怖主义罪行起诉了相当多的与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有关的人。由于其他文章已经对这些情况做了很全面的介绍,因此在此不作考虑:例如,见Todd Landman, “Imminence and Proportionality: The U.S. and U.K. Responses to Global Terrorism”, California Western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Vol. 38, No. 1, 2007; K. N. Trapp, “The Intera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Suppression Regime and IHL in Domestic Criminal Prosecutions: The UK Experience”, in D. Jinks, J. Maogoto and S. Solomon (eds), Applying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in Judicial and Quasi-Judicial Bodies, T.M.C. Asser Press, The Hague, 2014。
- 11欧洲一个名为“种族灭绝网络”的检察官网络编写了一份报告,讨论了不仅以恐怖主义罪行调查和起诉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和恐怖组织其他成员,而是还以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灭绝种族罪对其进行调查和起诉的机会: “Cumulative Prosecution Of Foreign Terrorist Fighters for Core International Crimes and Terrorism-Related Offences”, Eurojust, May 2020, available at: https://www.eurojust.europa.eu/sites/default/files/Partners/Genocide/20…。
- 12《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习惯法研究》,前注8,规则156。
- 13《日内瓦第一公约》第3条和第50条;《日内瓦第二公约》第3条和第51条;《日内瓦第三公约》第3条和第130条;《日内瓦第四公约》第3条和第147条;《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第一附加议定书》,1125 UNTS 3,1977年6月8日(1978年12月7日生效)(《第一附加议定书》),第11条和第85条;《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1125 UNTS 609,1977年6月8日(1978年12月7日生效)(《第二附加议定书》)。
- 14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习惯法研究》,前注8。
- 15同上注,规则158。
- 16《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51 条第2款;《第二附加议定书》第13条第2款;《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习惯法研究》,前注8,规则2。
- 17ICTY, Prosecutor v. Stanislav Galic, Case No.: IT-98-29-T, Judgement and Opinion, Trial Chamber, 5 December 2003.
- 18Ibid., para. 133.
- 19《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联合国第A/CONF.183/9号文件,1998年7月17日(2002年7月1日生效)(《罗马规约》)。
- 20同上注,第8条第2款第2项第1目和第8条第2款第5项第1目。
- 21关于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犯下战争罪的可能性,见ICC, Situ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Mali, ICC-01/12, available at: https://www.icc-cpi.int/mali; ICC, Situation in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Afghanistan, ICC-02/17, available at: https://www.icc-cpi.int/afghanistan; 关于叙利亚,见《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联合国第A/HRC/45/31号文件,载: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G20/210/89/PDF/G2021089.p…;关于伊拉克,见《2019 年 5 月 17 日特别顾问兼促进对达伊沙/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所犯罪行追究责任的联合国调查组组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联合国第S/2019/407*号文件,2019年5月17日,载: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19/139/36/PDF/N1913936.p…。
- 22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联合国第A/HRC/25/65号文件,2014年2月14日,载: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G14/109/23/PDF/G1410923.p…,第1页。
- 235月17日的信,前注21。
- 24L. Khalil and R. Shanahan, above note 3, pp. 2 and 3.
- 25ICC, Office of the Prosecutor, Situation in Mali: Article 53(1) Report, 16 January 2013, available at: https://www.icc-cpi.int/itemsDocuments/SASMaliArticle53_1PublicReportEN….
- 26ICC, The Prosecutor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Fatou Bensouda, Requests Judicial Authorisation to Commence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Situation in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Afghanistan, 20 November 2017, available at: https://www.icc-cpi.int/Pages/item.aspx?name=171120-otp-stat-afgh; ICC, Afghanistan: Situation in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Afghanistan, ICC-02/17, available at: https://www.icc-cpi.int/afghanistan.
- 27See T. Ferraro, above note 2.
- 28荷兰的一份技术报告发现:“完全投入且仅关注一个特定的组织(伊斯兰国)在特定时期(2013年至今)、特定地理区域(哈里发国)所犯下的一种国际罪行(种族灭绝),使得一系列可能犯下的其他国际罪行没有被追究,并可能逍遥法外。”Thijs B. Bouwknegt, Investigation, Prosecution and Trial of International Crimes in the Netherlands, 26 August 2019, p. 8. 澳大利亚也对其特种部队在阿富汗的行动展开了战争罪调查,而且不可能将此类罪行指控为恐怖主义罪行:Inspector-General of the Australian Defence Force, Afghanistan Inquiry Report, 2020, available at: https://afghanistaninquiry.defence.gov.au/sites/default/files/2020-11/I…。
- 29Australian Criminal Code Act 1995 (as amended) Schedule Criminal Code, Division 268, section 268.121.
- 30Anna Hood and Monique Cormier, “Prosecuting International Crimes in Australia: The Case of the Sri Lankan President”, Melbourn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3, No. 1, 2012, p. 7.
- 31Mali: Law n°08-025 of 23 July 2008; Law n°2016-008 of 17 March 2016; Netherlands: Criminal Code of the Kingdom of Netherlands (1881, amended 2012) and war crimes (Mali: Mali Penal Code (2001); Netherlands: Netherlands International Crimes Act (2003)).
- 32马里于2000年8月16日批准了《罗马规约》,并从2012年1月起将其境内的情势提交给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可对自2002年7月1日起在马里境内或由其国民犯下的《罗马规约》所列罪行行使管辖权:ICC, Mali: Situ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Mali, ICC-01/12, available at: https://www.icc-cpi.int/mal;2020年3月5日,国际刑事法院上诉分庭一致决定授权检察官开始调查法院管辖范围内与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局势有关的被控罪行:ICC, Afghanistan: Situation in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Afghanistan, ICC-02/17, available at: https://www.icc-cpi.int/afghanistan。
- 33ICTY, above note 17, para. 118.
- 34 《阿富汗刑法典》(2017年):在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第339条第22款,也可以说是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第340条第1款第1项或第2款。《澳大利亚刑法典法》(1995年,经修订)附表《刑法典》第268条:在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第268条第59款~第64款;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第268条第71款。《马里刑法典》(2001年):在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第31条第9款第19项;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第31条第9款第29项。《荷兰国际罪行法》(2003年):在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第5条第3款第1项;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第6条第2款第1项。
- 35《阿富汗刑法典》(2017年):在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第339条第10款;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第340条第1款第1项。《澳大利亚刑法典法》(1995年,经修订)附表《刑法典》第268条:在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第268条第47款;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第268条第71款。《马里刑法典》(2001年):在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第31条第9款第8项。《荷兰国际罪行法》(2003年):在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第5条第2款第2项第2目;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第6条第1款第1项。
- 36《阿富汗刑法典》(2017年):在国际性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第339条第1款第1项。《澳大利亚刑法典法》(1995年,经修订)附表《刑法典》第268条:在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第268条第35款;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第268条第77款。《马里刑法典》(2001年):第31条第9款第1项。《荷兰国际罪行法》(2003年):在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第5条第5款第1项;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第6条第3款第1项。
- 37《阿富汗刑法典》(2017年):在国际性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第339条第1款第4项。《澳大利亚刑法典法》(1995年,经修订)附表《刑法典》第268条:在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第268条第3款;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第268条第79款。《马里刑法典》(2001年):第31条第9款第2项。《荷兰国际罪行法》(2003年):在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第5条第5款第15项;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第6条第3款第3项。
- 38《阿富汗刑法典》(2017年):在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第337条第2款;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第340条。《澳大利亚刑法典法》(1995年,经修订)附表《刑法典》第268条:在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第268条第25款;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第268条第73款。《马里刑法典》(2001年):第31条第2款。《荷兰国际罪行法》(2003年):在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第5条第1款第2项;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第6条第1款第1项。
- 39Decree on the Intention not to Become a Party to the Rom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16 November 2016, Russian Federation, ICC Legal Tools Database, available at: https://www.legal-tools.org/doc/02c22f-1/.
- 40Available at: https://base.garant.ru/10108000/.
- 41《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966年12月16日,999 UNTS 171,联合国大会1966年12月16日第2200A(XXI)号决议通过(1976年3月23日生效)。
- 42《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1984年12月10日,1465 UNTS 85,联合国大会1984年12月10日第39/46号决议通过并开放供签署、批准和加入(1987年6月26日生效)。
- 43见前注34~38和上文关于俄罗斯联邦的讨论。
- 44例如,见联合国安理会信函和附件,《关于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的指导原则》,联合国第S/2015/939号文件,2015年12月23日;联合国安理会信函和附件,《关于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指导原则增编》,联合国第S/2018/1177号文件,2018年12月28日。
- 45TRIAL International, Universal Jurisdiction Annual Review 2020: Terrorism and International Crimes: Prosecuting Atrocities for What They Are, 30 March 2020, available at: https://trialinternational.org/wp-content/uploads/2020/03/TRIAL-Interna…, p. 14.
- 46 《反国际恐怖主义全面公约草案》,附录二,《2005年8月3日第六委员会主席给大会主席的信》,联合国第A/59/894号文件,2005年8月12日(《全面公约草案》)。
- 47Mahmoud Hmoud, “Negotiating the Draft Comprehensive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Major Bones of Conten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Vol. 4, No. 5, 2006, p. 1035.
- 48见《全面公约草案》,前注46,第20条。
- 49Measures to Eliminate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Report of the Working Group, Sixth Committee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UN Doc. A/C.6/60/L.6, 14 October 2005, available at: https://undocs.org/en/A/C.6/60/L.6, p. 6.
- 50Antonio Cassese, “The Multifaceted Criminal Notion of Terrorism in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Vol. 4, No. 5, 2006, p. 944.
- 51See, e.g., Kai Ambos, “Judicial Creativity at the Special Tribunal for Lebanon: Is There a Crime of Terrorism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Leide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24, 2011.
- 52Special Tribunal for Lebanon, Interlocutory Decision on the Applicable Law: Terrorism, Conspiracy, Homicide, Perpetration, Cumulative Charging, STL-11-01/I/AC/R176bis, 16 February 2011, para. 85.
- 53Ibid., para. 86.
- 54Ibid., para. 89.
- 55根据国际犯罪数据库,2015年至2020年期间有25项恐怖主义定罪,载:http://www.internationalcrimesdatabase.org/SearchResults/?q=&cat=10&fy=…;但是,根据表1展示的来自单个国家的资料,数据远多于此。
- 56资料来源:TRIAL International Database, available at: https://trialinternational.org/resources/universal-jurisdiction-database; International Crimes Databases, available at: http://www.internationalcrimesdatabase.org/; TRIAL International Universal Jurisdiction Annual Review, available at: https://trialinternational.org/wp-content/uploads/2020/03/TRIAL-Interna…, https://trialinternational.org/wp-content/uploads/2019/03/Universal_Jur…, https://trialinternational.org/latest-post/make-way-for-justice-4-momen…, https://trialinternational.org/wp-content/uploads/2017/03/UJAR-MEP_A4_0…, https://trialinternational.org/wp-content/uploads/2016/05/UJAR_2016.pdf.
- 57ICC, The Prosecutor v. Ahmad Al Faqi Al Mahdi, 27 September 2016, Trial Chamber, Doc No. ICC-01/12/-01/15-171, available at: https://www.icc-cpi.int/CourtRecords/CR2016_07244.PDF; Extraordinary Chambers in the Courts of Cambodia, Case 002/02, Judgement, Trial Chamber, 16 November 2018, Doc. No. 002/19-09-2007/ECCC/TC, available at: https://www.eccc.gov.kh/en/document/court/case-00202-judgement.
- 58资料来源:Russian Federation Statistical databases, available at: http://eng.rosstat.gov.ru/.
- 59根据作者存档的研究。
- 60除了美国的国别报告之外,很难找到任何关于马里和阿富汗法院判决的全面信息。非政府组织的报告也提到了法院所作的努力,但没有提供任何值得收录的具体统计数据。因此这些数据并不完整。
- 61基于美国的《各国反恐怖主义报告》。关于2016年的数据,见https://www.state.gov/wp-content/uploads/2019/04/crt_2016.pdf,第39~41页;2017年,见https://www.state.gov/wp-content/uploads/2019/04/crt_2017.pdf,第29页;2018年,见https://www.state.gov/wp-content/uploads/2019/11/Country-Reports-on-Ter…,第30页;2019年,见https://www.state.gov/wp-content/uploads/2020/06/Country-Reports-on Terrorism-2019-2.pdf。2016年(第238页)和2017年(第169页)的报告指出,总检察长办公室起诉了一些恐怖主义罪行,并重点强调了总共六个特定案件。随后的报告没有提到具体案件,但暗示有许多案件(2019年报告,第152页)。
- 62根据作者在阿富汗专门从事刑事诉讼工作的一线经验。
- 63澳大利亚和荷兰(这两个国家有最准确的法院报告)的起诉是针对与武装冲突局势有关的行为,即在发生武装冲突的领土上作为一个“恐怖主义”组织的所谓成员。其他未列入的起诉是对诸如资助恐怖主义、同谋实施国内恐怖袭击或实际参与国内恐怖袭击等行为的起诉。
- 64 2017年10月至2020年的案例,载:https://csd.njca.com.au/recent-cases/#PID_8118;2015年至2017年的案例来自对所有澳大利亚判例法的检索,载:http://www.austlii.edu.au/advanced_search.shtml。
- 65见前注60。
- 66根据2016年、2017年、2018年和2019年美国的《各国反恐怖主义报告》,前注61。2017年,据报道:“政府在2017年针对69起与恐怖主义有关的案件进行开庭审理,并因与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拘留了30人。资源紧绌、缺乏调查技术培训以及审判恐怖主义案件的经验不足困扰着薄弱的司法系统。马里政府从头到尾都没有对任何恐怖分子进行调查、起诉和判刑”。(第29页)
- 67依据是所涉及的所有其他案件均为零,而且国际刑事法院正在调查马里,但在这方面没有公开报道其他的国内案件。
- 68见前注63。
- 69统计数据来源于2015年1月至2018年4月荷兰向欧盟刑事司法合作署(Eurojust)的恐怖主义定罪监测所作的声明(第22-32期)。此后这些数据便停止公布。第22期,2015年1月至4月,见(六项定罪);第23期,2015年5月至8月,见https://www.eurojust.europa.eu/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Reports…(两项定罪);第24期,2015年9月至12月,见https://www.eurojust.europa.eu/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Reports…(九项定罪);第25期,2016年1月至4月,见https://www.eurojust.europa.eu/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Reports…(六项定罪);第26期,2016年5月至8月,见https://www.eurojust.europa.eu/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Reports…(15项定罪);第27期,2016年9月至12月,见https://www.eurojust.europa.eu/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Reports…(12项定罪);第28期,2017年1月至4月,见https://www.eurojust.europa.eu/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Reports…(六项定罪);第29期,2017年5月至8月,见https://www.eurojust.europa.eu/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Reports…(八项定罪); 第30期,2017年9月至12月,见https://www.eurojust.europa.eu/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Reports…(12项定罪);第31期,2018年1月至4月,见https://www.eurojust.europa.eu/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Reports…(六项定罪);第32期,2018年5月至8月,见https://www.eurojust.europa.eu/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Reports…(22项定罪)。
- 70Tjitske Lingsma, “First Dutch Islamic State Fighter Convicted For War Crimes”, Justice Info Net, 25 July 2019, available at: https://www.justiceinfo.net/en/42008-first-dutch-islamic-state-fighter-…; Oussama Achraf Akhlafa, Guus K Court of Appeal, 21 April 2017; Eshetu Alam, District Court of the Hague 2 March 2018, Case No. 09/748003-18v.
- 71事实上,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Scott Morrison)已经宣布,人们将无法回国:见Prime Minister of Australia, Transcript - Radio Interview with Oliver Peterson, 6PR, Media Release, 22 October 2019, available at: https://www.pm.gov.au/media/transcript-radio-interview-oliver-peterson-…。
- 72Carl Lampe, “Russia's Repatriation of ISIS Members”, 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12 April 2019, available at: https://www.fpri.org/article/2019/04/russias-repatriation-of-isis-membe….
- 73Muslim Ibragimov and Alexander Ivanov, “Chechen Fighters Enter Syria through Azerbaijan, Interior Ministry Spokesman Says”, Caucasian Knot, 20 September 2013, available at: https://www.kavkaz-uzel.eu/articles/230371?redirected=www.kavkaz-uzel.ru.
- 74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 Foreign Fighters: An Overview of Responses in Eleven Countries, Zurich, March 2014, available at: https://css.ethz.ch/content/dam/ethz/special-interest/gess/cis/center-f…, p. 14.
- 75Prosecutor v. Maher H., District Court of The Hague, The Netherlands, 09/767116-14, 2 December 2014.
- 76District Court of The Hague, 23 July 2019, reference 09/748003-18 and 09/748003-19.
- 77Treatment of Foreign Fighters in Selected Jurisdictions: Country Surveys, available at: https://www.loc.gov/law/help/foreign-fighters/country-surveys.php.
- 78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 above note 74, p. 18.
- 79Kerstin Braun, “‘Home, Sweet Home’: Managing Returning Foreign Terrorist Fighters in Germany, The United Kingdom and Australia”,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Law Review, Vol. 20, No. 3–4, 2018, p. 318.
- 80Ibid., p. 328.
- 81Roshan Noorzai, “Afghanistan to Discuss Fate of Foreign IS Prisoners with Their Countries”, VOA News, 3 May 2021, available at: https://www.voanews.com/extremism-watch/afghanistan-discuss-fate-foreig….
- 82Mark A. Drumbl, Atrocity, Punishment and International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2007, p. 2.
- 83Ibid., p. 3.
- 84Jan Christoph Nemitz, “The Law of Sentencing in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The Purposes of Sentencing and the Applicable Method of Determining the Sentence”,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4, 2001, p. 89.
- 85Ibid.
- 86Ibid.
- 87Ibid., p. 91.
- 88Jonathan Hafetz, “Diminishing the Value of War Crimes Prosecutions: A View of the Guantanamo Military Commiss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Cambridg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Vol. 2, No. 4, 2013, p. 808.
- 89Editorial, “Responding to Terrorism: Crime, Punishment, and War”, Harvard Law Review, Vol. 115, No. 4, 2002, p. 1229.
- 90Ibid., p. 1231.
- 91Gerhard Werle and Aziz Epik, “Theories of Punishment in Sentencing Decis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n Florian Jeßberger and Julia Geneuss (eds), Why Punish Perpetrators of Mass Atrocities? Purposes of Punishment in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2020, pp. 326–327; Michael Moore, Placing Blame: A Theory of Criminal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1997, p. 8; J. G. Murphy, “Legal Moralism and Retribution Revisited”, Criminal Law and Philosophy, Vol. 1, No. 1, 2007, p. 11.
- 92Frank Neubacher, “Criminology of International Crimes”, in F. Jeßberger and J. Geneuss (eds), Why Punish Perpetrators of Mass Atrocities? Purposes of Punishment in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2020, p. 28.
- 93Mark Tunick, Punishment: Theory and Practic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1992, p. 95.
- 94Mark A. Drumbl, “Victims who Victimise”, Lond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4, No. 2, 2016, p. 240.
- 95Michael Clark and Peter Cave, “Nowhere to Run?: Punishing War Crimes”, Res Publica, Vol. 16, No. 2, 2010, p. 200.
- 96Ibid., p. 201.
- 97J. C. Nemitz, above note 84, p. 91.
- 98Ibid., p. 92.
- 99Claire Finkelstein, “A Contractarian Approach to Punishment”, in Martin P. Golding and William A. Edmunson (eds), Blackwell Guide to the Philosophy of Law and Legal Theory, Blackwell Publishing, London, 2005, p. 208.
- 100K. Braun, above note 79, p. 329.
- 101M. Clark and P. Cave, above note 95, p. 201.
- 102Andrew Ashworth, Sentencing and Criminal Justi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2010, p. 84.
- 103UN Office of Drugs and Crime, Investigation, Prosecution and Adjudication of Foreign Terrorist Fighter Cases for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2018, available at: https://www.unodc.org/documents/terrorism/Publications/FTF%20SSEA/Forei…, p. 31.
- 104强奸和侵害妇女的性暴力也受到妇女特别法——2009年《消除针对女性暴力法》的管制,且刑罚更加严厉:判处20年至30年以上的监禁或死刑。
- 105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 above note 74, p. 12.
- 106K. Braun, above note 79, p. 326.
- 107H. Højfeldt, “Prohibiting Participation in Armed Conflict”, Military Law & Law of War Review, Vol. 54, 2015, p. 30.
- 108《罗马规约》,前注19,序言。
- 109Marnie Lloydd, “Challenges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Obligation to Ensure Respect for IHL – Foreign Fighting as an Example”, in Eve Massingham and Annabel McConnachie (eds), Ensuring Respect for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Routledge, London, 2020, p. 241.
- 110J. Hafetz, above note 88, pp. 816–817.
- 111ICTY, Prosecutor v. Delalic et al., Case No.: IT-96-21-T, Trial Chamber Judgment of 16 November 1998, para. 1234.
- 112ICC, Prosecutor v. Katanga Art. 76 Decision ICC-01/04-01/07-3484, 25 May 2014, para. 38; Sergey Vasilev, “Punishment Rationales in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risprudence”, in F. Jeßberger and J. Geneuss (eds), Why Punish Perpetrators of Mass Atrocities? Purposes of Punishment in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2020, p. 70.
- 1132019年5月17日的信,前注21,第4页。
- 114ICTY, above note 111.
- 115Ibid., p. 241.
- 116Ibid.
- 117M. Lloydd, above note 109, pp. 233–234.
- 118K. Braun, above note 79, p. 327.
- 119T. B. Bouwknegt, above note 28, p. 20.
- 120Mark Lattimer, Shabnam Mojtahedi and Lee Anna Tucker, A Step Towards Justice: Current Accountability Options for Crimes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Committed in Syria, Ceasefire Centre for Civilian Rights and Syria Justice and Accountability Centre, May 2015, p. 24.
- 121T. B. Bouwknegt, above note 28, p. 39.
- 122Ibid.
- 123K. Braun, above note 79, pp. 328–329.
- 124Vasko Nastevski, “The Australian Experience of Conducting War Crimes Trials”, in Jadranka Petrovic (ed.), Accountability for Violations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Essays in Honour of Tim McCormack, Routledge, London, 2016, p. 222.
- 125Inspector-General of the Australian Defence Force, above note 28.
- 126Adam Cooper, “Safety Fear for Afghan Villagers Raised in Ben Roberts-Smith Case”, Sydney Morning Herald, 7 May 2021, available at: https://www.smh.com.au/national/safety-fear-for-afghan-villagers-raised….
- 127M. Lattimer, S. Mojtahedi and L. A. Tucker, above note 120.
- 128TRIAL International, above note 45, p. 14.
- 129Ben Saul, “Crimes and Prohibitions of ‘Terror’ and ‘Terrorism’ in Armed Conflict: 1919–2005”, Humanitäres Völkerrecht – Informationsschriften /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of Peace and Armed Conflict, Vol. 4, 2005, p. 276.
- 130TRIAL International, above note 45, p. 14.
- 131See T. Ferraro, above note 2.
- 132See Thomas Van Poecke, Frank Verbruggen and Ward Yperman, “Terrorist Offenc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Exclusion Clause: Belgium as the Odd One Out”,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2021, in this edition.
- 133M. Lloydd, above note 109, p. 241.
- 134K. H. Kaikobad, above note 5, p. 228.
- 135Ashley Deeks, “Domestic Humanitarian Law: Developing the Law of War in Domestic Courts”, in Derek Jinks, Jackson N. Maogoto and Solon Solomon (eds), Applying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in Judicial and Quasi-Judicial Bodies: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Aspects, Springer, London, 2014, p. 138.
- 136TRIAL International, above note 45, p. 13.
- 137See, e.g., Anthony Whealy, “A Judicial Perspective: Surveillance Evidence and the Right to a Fair Trial”, in Fergal Davis, Nicola McGarrity and George Williams (eds), Surveillance, Counter-Terrorism and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ism, Routledge, London, 2013; Clive Walker, “Terrorism Prosecutions and the Right to a Fair Trial”, in Ben Saul (ed), Research Handbook on International Law and Terroris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Cheltenham, 2020.
- 138K. H. Kaikobad, above note 5, p. 276.
- 139TRIAL International, above note 45, p. 13.
